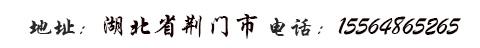丰收节丰收的季节总是伴随着欢乐,也总是伴
|
北京荨麻疹医院那里好 http://m.39.net/pf/a_9159711.html 文/耿桂栩 去年夏天,儿子问我,爸爸,麦子是什么样的?我和他妈妈商量以后,决定带他回老家去麦田看麦子。 根据我小时候的记忆,六月初,正是风吹麦浪满地金黄的季节。 我们从济南出发,一路开到沂蒙山,那里曾经有我跟着父母播种、收割的稚嫩身影。我想站在那一片麦田里,自豪的对儿子说,儿子,爸爸小时候,就曾经在这里挥洒汗水。 但是,没有看到麦田。 看到的是成片的桃园、葡萄架、苹果树。 看来,老家丰收季的内容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麦子、玉米、花生、地瓜,而是剪枝、授粉、套袋、采摘了。 但我还是很怀念那起伏的麦浪,鲜嫩的玉米“胡子”,花生开花后花柄悄悄钻进土里长成饱满的果子,地瓜把地垄撑出宽宽的裂缝。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,常常是开始收麦子的日子。在学校开完了联欢会,我们就打着彩纸糊的小旗子,直奔自家的麦田了。麦田里,已经站立了一个个麦捆,母亲从麦地里站起来,手里拿着镰刀,肩膀上搭着毛巾。我和姐姐、父亲,就加入收割的队伍了。父亲在学校教书,要和我们一样等联欢会结束了才来。 小朋友并不因为年纪小而略闲一闲,大人在干活的时候,也是必须跟上节奏的。大人一镰刀割三垄,小孩可以割一垄,实在累得割不动了,就去捡麦穗。 太阳也似乎因为丰收而兴奋。 地里毫无避阴的地方。 麦芒扎在身上,又刺又痒。 幸好麦田的旁边便有水,大股的水流哗啦啦的从麦地不远处的泉眼里流出来,绕过麦田,转过山脚,流进马莲河,汇入沂河,融进大海去了。夏天的泉水不像冬天的那么蒸汽腾腾的温热,夏天的泉水刺骨的凉。我们在麦地里淋漓的冒够了汗,就奔着泉水去了,把脚插进水里,水淹没了膝盖。把毛巾饱饱的蘸满水,甩到背上去,一声脆响,一个激灵。 午饭就在地头吃。一家人围着一个铺在地上的花包袱,包袱上放着早晨从家里带出来的煎饼、咸菜,有时候有炒鸡蛋。 麦地里,挥汗如雨是小孩儿不喜欢的。但如果有几只蚂蚱飞来,小孩儿们必然会忘了毒太阳,欢叫着追逐它,捉住它,用一根狗尾巴草串起来,晚上回家放在灶火上烤一烤,那也是让人心花怒放的美味。麦地里有许多别处少见的植物:瓜蒌,那是一种能长出圆圆的像小甜瓜一样的多年生草本藤状植物;王不留行,开一种紫红色的花,有点像石竹;地边有野李子,矮矮的一簇植株,开粉红色的小花,果子像现在超市里卖的车厘子,有趣的是,我们也把它叫做“车厘子”,但明显不是同一种水果…… 割麦子的时候,麦垄里玉米已经发芽了。玉米和麦子轮作,在麦子收割之前,玉米已经下种,到九月份,就也到了收获的季节。玉米叶子带着锋利的芒刺,掰玉米的时候,剌在胳膊上,火辣辣的疼。 玉米收回家,堆在天井里,小山一样。晚上,吃了饭,一家人坐着马扎,围着玉米堆剥玉米,父亲和母亲偶尔会对几句《沙家浜》的唱词。我们把玉米棒子外面包裹着的萼片一片片剥下来,最后留下几片,每两个玉米系在一起,也可以辫成长长的一串,像一挂放大的鞭炮,搭在院子里的杨树上、木架子上、墙头上,满院子里都装饰成了金黄的色调。 再过几天,花生成熟了,沙土地里的花生,一头刨下去,嘟噜噜的果子现身了,抖着身子,等着你把他摘下,剥开,放进嘴里,嚼出香甜的乳白色的汁水。小孩儿们更喜欢那种尚未成熟的果子,花生的果壳肥厚多汁,甜甜的,像一种鲜美的水果。这“水果”,太阳一晒,就咬不动了。 早晨,地上偶尔有了薄薄的霜花,到了收地瓜的季节了。地瓜就地切成片,晾晒在地里。这时候,你到田野里去看吧,山川穿上了白色的纱裙,纱裙上有绿色的叶子,那是一片翠柏,有黄色的小花,那是一行钻天杨。一阵风,刮来几片云,落下几点雨,人们急急忙忙把地里的地瓜干一片片地捡起来,装进麻袋,运回家。太阳出来了,半干的地瓜干又被抬出来,铺在场院里晾晒。 …… 丰收的季节总是伴随着欢乐,也总是伴随着劳累和辛酸。 我给孩子讲了这么多关于劳作、关于收获的故事,孩子并不懂,他喜欢树上的苹果、葡萄、桃子。水果也要陆续成熟了,乡亲们也要忙着采摘了。 又是一番丰收的喜庆景象! 万亩桃园里掩映的村庄。摄影:耿桂栩 注:封面图片来源于新华网。 壹点号老耿读书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,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。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guangdongwanga.com/gdwblxfb/2417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围剿与反围剿发达国家如何绞杀中国制造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